这几天一直去吃一家叫“社员饭铺”的苍蝇馆。
饭铺的位置很奇妙,在一个我一句话说不出来的地方。
很容易得知天府新区这块以前是一片鸟不拉屎的荒地,HRBP跟我聊天时也说“以前成都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这里很偏。
但现在上班呢,十分钟的骑行路程,其间就已经有千军万马从自己住的大小房子里出发,驾着共享单车、公路车、电动车、电动滑板车、摩托车、电车、油车,操着各路防晒的听歌的办公的设备,沿着四通八达的大路小路,日复一日杀去产业园蹲号。
下班的时候呢,人稍微稀疏些,因为有些公司还有wlb,所以早早的有人迎着四川盆地刺眼的golden hour,眼睛眯着但是嘴笑嘻了,精神百倍、挺着身板离开;遇到放人稍晚点的公司,小蚂蚁们就披着晚霞回家,只是肚子有些饿了;再加班的人就没办法了,回去只能迎路撞上那些收拾着准备打烊的路边摊三轮车、吃完饭腆着肚子全身都是酒气汗味的叔叔们、在街边大草坪里玩的小狗。
很多人和很多基础设施,看上去都非常摩登,想要什么都是触手可及。咖啡、沙拉,各式快餐。人造的河流、湖水,桥梁、楼栋。再换句话说,这个地方跟上海(或者很多城市的很多地方)其实没什么两样,在天府和在漕河泾,有什么区别吗?我没法感知,大部分时间我感到我的生命力不再鲜活。
社员饭铺也在这样的天府新区里。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没入职,对这个我选择要留下暂且生活的地方还存有一些新鲜的想象。虽然不敢把这些想象再细化,但我仍相信成都是包容的,有情的,和我小时候常来居留的那个城市别无二致。于是我骑着滚烫的共享单车,在墨镜聊胜于无的保护下两只眼睛死盯着太阳,寻着导航骑到了社员饭铺门口。

没想这儿其实是一个安置小区,是个在深圳那边可能随处可见的城中村。每栋楼都又高又烂又挤,浅蓝色的竖长瓷砖堆叠向上,好像个空置许久无人料理的垂直游泳池。我无从得知那些楼房里有多少双眼睛望着同一方铁架子窗。当然顶楼还有私搭的铁棚,该住人的住人,该种菜的种菜。
村里边儿“原始”的东西应有尽有。菜市场,卖新鲜的不知道从哪来的菜肉,这几天卖的也都是那几样;也卖许多熟制品,卤菜烤鸭炸鸡;还卖半成品,碱面米线豆干苕皮,火锅底料和泡姜泡海椒;还卖服务,修鞋补衣服之类的;情趣店、电动车店、麻将馆、茶馆,具体还卖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当然还有汇集了五湖四海美食小吃、从早饭包到夜宵的店面、小摊、外卖,我没听说过的香酥鸭,我找遍重庆都吃不到的猪儿粑,我最喜欢的糯米凉虾,老公馋了很久的胡辣汤,还有那种一闻就全是油盐味精但肯定很好吃的农村味家常菜,饭是用长方形的盆装的,菜就用乡宴上随处可见的白瓷碗盛着,还没去试过。
村里边儿的人也是那样的,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千奇百怪,有着万门技艺,修车卖车、装修糊墙、做菜卖饭,保不齐那些紧闭落灰的卷帘门后也藏了些违章生意。但都只有同一种劳动人民的样貌,皮肤黝黑,做事干练。衣衫鞋袜应是穿了许久的来自批发城的货品,上边印着没人能看明白的符号,能指与所指,比比皆是的abidas,new barlons,走两步就踩到白色垃圾、口痰或香蕉皮。
社员饭铺就在这个安置小区的门口。小区外沿街的地方已经被gentrified得差不多了,都是些修得还算富丽堂皇的中餐店,路牙子上也总会停几辆载着大小老板们前来聚餐的豪车,再到马路上就是违停的但怀旧的三轮车(我就经常打三轮去吃!现在的三轮车老豪华了,皮质软座呢),以及胡乱摆放的七彩共享单车。隔着马路对面就望着高档小区,而饭铺背后、进到安置小区,就是这些劳动人民。
工作日和周末又都去了几次社员饭铺,最终把想吃的菜品都吃了个七七八八,但见到的总是以上同一副光景。粉蓝澄澈的晚霞在这儿被油烟冲得浑浊,工业化的汽车轰鸣在这儿被拥堵的人流与三轮车流淹没,门店摊位里的饮食在黄昏的光线中显得越发活泼,前来消遣的人的身份就这样被兑得普通平凡。
社员饭铺开在这个安置小区门口就像个滤网,把现代的东西都滤在外面,把过时的东西都留在里面,但又不得不揽了些现代的东西滞存在滤网里。店里的陈设就是这样——没有空调,就几扇挂在墙上的黑色大风扇随意转转,室内外几组被盘得包浆的高矮桌椅随意摆摆,破烂的遮光架随意支支,要来就坐,不来也随你便。里头的厨房连基础的排气都没做明白,爆炒的油烟就从厨房里钻出来在高吊顶的屋堂里飘荡,见到一个鼻孔就往里钻,死活就是不飘出去。墙上贴的都是些“公社”类型的宣传张贴,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有些年头了。但覆盖在这些破烂张贴上的,又是两个放得超级大的收款码,一个蓝底,一个绿底,排排贴在一起,占了半面墙,这样所有人无论远近都能举着手机自觉付钱了。
来社员饭铺吃饭的人也承接了社员饭铺滤网般的特质。多数是安置小区的居民,蓝领的叔叔,一般和他们的哥们儿一起,因为大家都没讨到老婆。他们通常穿着白色灰色的汗衫,还没开始吃饭就把衣服脱了个精光,雕琢着劳动后留下的浅浅腹肌纹路的大肚皮一甩一甩,汗水就跟着一甩一甩。还有好些是看了抖音探店的年轻人,穿着睡衣或者写着自己名字的球衣慢悠悠来吃了又慢悠悠走,有小孩的就把小孩放在旁边让他们无助地哭,哭累了再上坐吃饭。最后剩了些打扮潮流穿着decent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小布尔乔亚的人,他们一开始都会站在店门口诚惶诚恐地朝里看,没有座位坐的时候也不愿意拼桌,手里举着冰块已经被晒化了的蜜雪冰城,坐上桌的时候得抽至少三张餐巾纸自觉把桌椅再擦一遍,点菜的时候还得举着手机对比一下大众点评上的推荐菜,但为数不多的评论和数据看一眼又觉得没什么好参考的,得磨叽十分钟才能选好一桌菜,上菜后拍照,扒饭,行云流水,最后评价道,这里的味道有点太咸。

饭铺的菜单,可能只有对川菜有业余以上研究的人才能解读出个中逻辑。凉拌、盐煎、水煮、泡椒、红烧、炝炒、蒜蓉,这些味型在饭铺里都有。最好吃的我想应该是鱼香,这也是他们的招牌味型。我吃遍大江南北最讨厌的就是商业化的鱼香,沾一口红芡就只能吃出极为普通的糖醋味,所以走到哪都不愿意再尝一口鱼香和糖醋的菜。直到后来看了川菜师傅的短视频才知,鱼香的味型原本来自装了一条鱼来提鲜味的泡菜坛中的泡姜泡椒泡豇豆,出锅时还会混入切碎的藿香来增添香草滋味,这样一听,觉得鱼香真的很好吃。第一次在饭铺吃的时候就点了一份鱼香肘子,用勺子舀红亮油滑的芡,里面均匀地悬浮着泡豇豆和藿香,拌一口饭莽进嘴里,发酵的泡菜、淡雅的鱼鲜、奇异的藿香、浅浅的辣感,舌头和脑子都还来不及品,就哧溜一下全部滑进胃里,所以食客通常会扒完一大碗饭才能吃明白这个暗藏玄机的鱼香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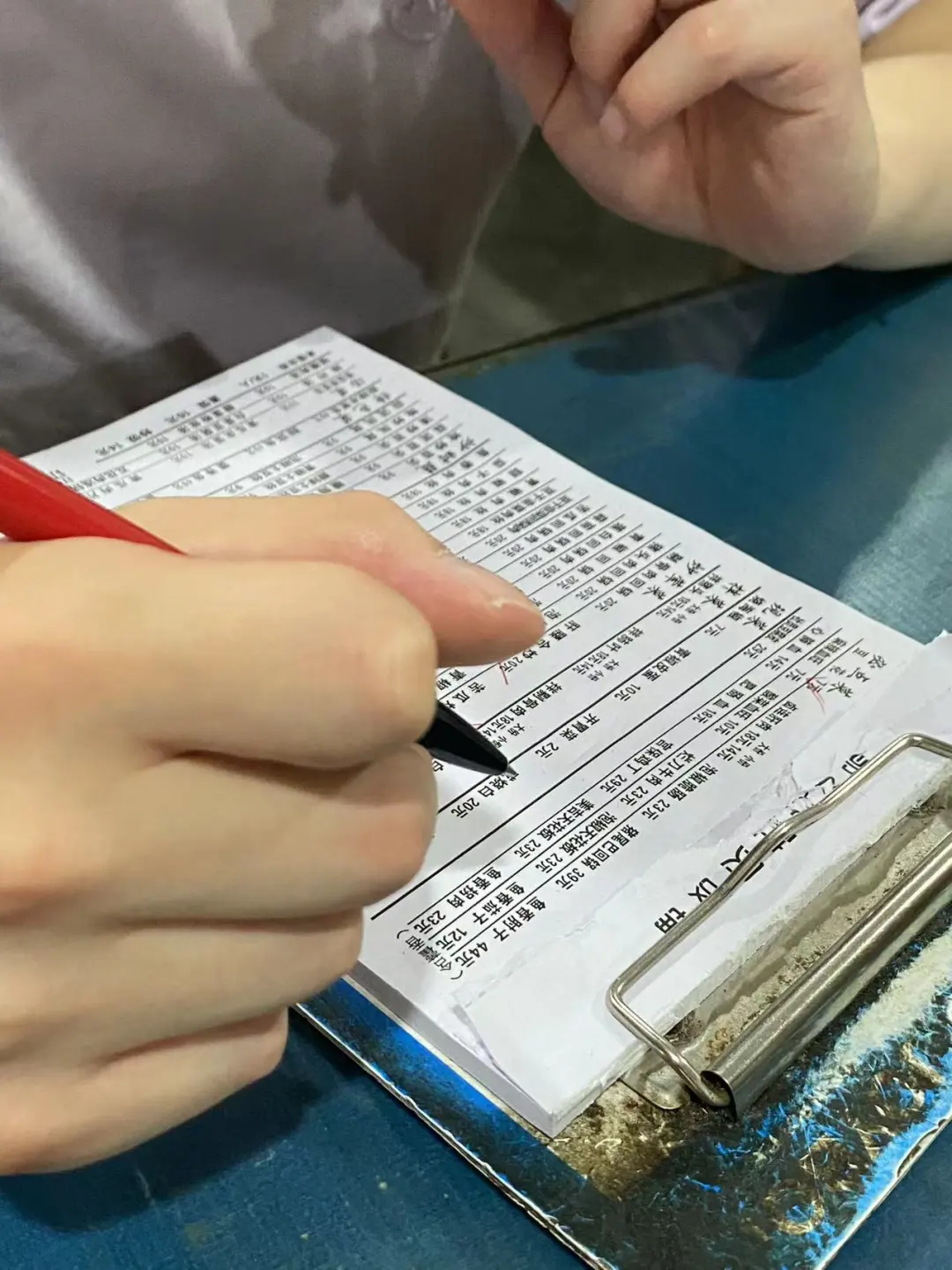
除了味型有趣,这里的食材也金鸡独立。炒菜店经典的肝腰合炒、水煮肉片。火锅店常吃的猪天堂,在这里能用泡椒炒。川渝嫌处理起来麻烦就索性不再吃的猪肺,在这里能凉拌爆炒熬汤。猪脑花,可以和豆腐或肉末一起烂炖,囫囵舀进碗里,也是嗦一下就不见了。会吃的人肯定知道这里的菜单不止这么些,很多菜都customizable,比如皮蛋就可以配上烧海椒吃,肉和内脏都可以混着炒,肉的形状也是可以定制的,肉馅肉丝肉片、滑肉酥肉坛子肉,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
吃饭的人往往看到菜单就已经饿得不行了,所以还没入座就把负责点菜的嬢嬢唤来,两下布置好任务,就很自觉地走去饭桶那儿给自己舀满满一大碗饭,筷子拆掉包装,在碗面上摆得心不在焉,就等着上菜开干了。

在等待的五分钟内,雾灰色的油烟持续从后厨窗口冒出,同样冒出的还有许多声音。底层的旋律是在灶台上的,我猜想墩子应该在笃笃笃地切菜,厨子在哗哗哗地颠锅,灶台就呼呼呼地冒火,锅里的菜滋啦啦地尖叫。人声嘛,就是厨子和传菜嬢嬢的怒吼。传菜的嬢嬢不知道站在哪,总之是从上班到下班都一直扯着嗓子大吼,就跟小学的时候生气的班主任那样的嗓门和语调,“三号!爆炒腰花!芹菜炒肉!” 厨子回应,“要得!” 或者“撒子安?你说清楚点嘛!一哈三号一哈五号!” 此外还有和声呢,食客稀里哗啦扒饭、叽里咕噜聊天,屋内大风扇噗噗噜噜地吹,室外电瓶车比比八八地叫。最好听的和声来自在桌椅间转悠的老板和承担店小二职务的叔叔嬢嬢们。每有一桌人吃完饭了,就拍下筷子大叫一声,“老板儿!给钱哦!” 这时候有空的老板和小二们就寻着声音走到桌前,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隔着积满油污的镜片,开始扫描食客桌面早已被横扫一空的碗盘——“烧椒七块拌菜十五二十二加一份腰花五十五十加二十二七十二两碗饭四块一瓶水两块一共七十八”——像这样一口气不歇,声调叮叮咚咚地唱完一曲,便拂袖而去。随后不知道藏在哪里的烂音响再发出一声“微信到账,七十八元”,标志着食客正式吃完一顿饭,音乐会就到此结束,只是无人出来谢幕。
所有生活在天府新区的人,操练着八仙过海般的阵仗杀去产业园的千军万马,还是这些每日在烈日下叫卖徘徊的安置居民,在这里都只是一个个大张着嘴的社员,很幸福地被困在一个简单的时空里。基础的买卖交易,带来值当的投资回报,中间不损耗太多时间与情感成本,怎么想来都是巴适的。
远离校园和友人,远离那些若有若无的迷离情欲,日复一日做着高强度的工作,逐渐见证自我被资本消磨——我以为回忆就像沙盘,他们与我都只需轻轻一抹,沙盘就平整如新。但我想这世界上总会有些我能把握住一个时段的东西,我会抓住它。